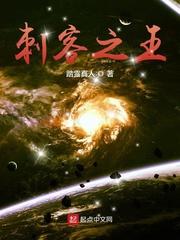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女帝的工程手册 > 第八十九章(第1页)
第八十九章(第1页)
坤宁宫寝殿内,皇后正在临窗赏玩一盆新贡的兰草,她身边的掌事宫侍正为她细细梳拢长发。铜镜中映出宫侍欲言又止的神情。
宫侍低声开口:“娘娘,太女殿下如今在前朝风头更盛。毕竟女儿身,只怕总有人心下不服,妄图从根子上动摇国本。咱们……是否该未雨绸缪,将后宫好生‘整治’一番?譬如几位得圣心、又或母族强盛的年轻妃嫔……”
皇后目光未离兰草,淡声道,“你跟着本宫多年,须知本宫的职责,乃是让这宫闱之中风平浪静,而非搅弄风云,无故生端。”
“太女之功,利在社稷,泽被生民,难有皇子得以企及。眼下之势,本宫与她麾下众人愈要持重,但求无过,则远胜于为她翦除一二隐忧。我等若能稳如磐石,便是对她最大的扶持了。”
“至于,从今往后,心思活络的,只要她们不敢真做出来,便由她们想去。”
---------------
一位经筵讲官的府邸里,其家族中某位将要出嫁的小姐的房间内,这位小姐与自己的贴身女侍一同绣着婚服。
那女侍时不时背过身偷偷抬手抹一下泪,在满室的沉默中犹豫了很久,还是有些哽咽地开口:
“小姐,薄身知晓,您心里装着万里山河,自幼就想习武,想当大将军,也看出这门亲事,并非您心之所向。”
“您为何,偏偏不肯将心事禀明太女殿下?殿下已为那么多高门贵女铺就前路,定然也会为您做主!您本可入殿下门下的学堂,名正言顺地习文练武……假以时日,何愁壮志难酬?届时,再觅一位真心敬您爱您的如意郎君,或是风光招赘,岂不美满?”
“可如今……婚期迫在眉睫。薄身愚钝,实在想不通您为何要独自隐忍,每每思及,都替您肝肠寸断。”
贵女半晌没应声,缓缓叹了口气,抚了抚手中嫁衣,开口时声音未见悲戚,却也沉闷。
“这滔滔江水,不因我一滴而盈;纳我微沤,亦如沧海容尘。既如此,又何须执念此水从何而来,如何而至,是雨是雪,又何问其形?”
女侍思索了一下,歪头疑惑,“薄身愚笨,没能领会小姐的意思。”
贵女勾唇笑笑,神态间愁色未褪,却更趋于平静,
“幼时欲习武,为父所阻,深以为憾,只觉身陷囹圄。及长渐悟,此身所在,虽为牢笼,亦为金玉铸就之安稳天地。然身为女子,或添一副厚重的枷锁镣铐。”
“笼中岁月,难免风侵雨蚀,沙砾磨身,偶有荆棘生出,伤人而不致命。而我亦非全然困于其中——我本已化入这牢笼几分,与其同构,与其共生。”
“放眼天下,女子万千,便有万千枷锁、万千囚笼。或有淬毒之铐,或有锈蚀之笼。各式镣铐彼此勾连,代代相传,腐朽如斯,却俨然难破。”
“今幸有太女殿下,率女子之身,携女子之心,愿挥剑斩此铁索连环,更以锁钥相授,启人牢门。”
“我信殿下。有她在,我便等得。纵已嫁作人妇,生儿育女,乃至白发苍苍,仍可持她所予之钥,启我枷锁。我更信她,纵不启此锁,他日亦能化铁笼为柔丝,转身之囚困为心之牵绊。”
“而今,我为文昌台经筵讲官之女,来日或为人妻、人母。更是陈家小姐,京城贵女。故我择此路,因除却此等诸般名姓,终了,我才是陈昭蘅。”
“而我,最该是陈昭蘅。”
“我信终有一日,无论置身何位,在一切之前,我先是陈昭蘅。届时,不论何时何境,陈昭蘅皆可读书明理,习武建功;可曲不离口,针线为伴;能安守一室,亦可行遍山河;可独身自立,亦可相夫教子。”
“我信彼日之临,届时方才所言种种道路,皆只是寻常之选。”
断断续续下了小半个月的春雨,细细密密,柔和得很,并不恼人。御河两岸官植的老梅,疏疏落落的几树,花已开到了尾声,间或旋下几片花瓣,无声地点在绿绸似的河水上。
今年的春猎,望远镜刚好就派上了用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