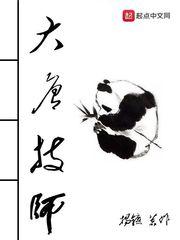六零小说>身为材料生的我却被推去做冲喜炮灰(穿书) > 第 26 章(第2页)
第 26 章(第2页)
顾放唇边牵起一抹温和笑意,缓声道:“此处的花木,与从前所见……似乎有些不同了。”
恰在此时,应白川也悠悠踱了过来,闻言随口接道:“是吗?我没吩咐人换过花啊,也许是下人们自己打理的吧,我倒没留意。”
林意:“……”
大哥,您真是钝感力超绝啊,听不出这话里有话吗?她暗暗扶额,赶紧岔开话头:“时辰不早了,咱们还是快些启程去瞧瞧水泥吧。”
顾放含笑望了林意一眼,从善如流:“也好。从此处过去,总需小半个时辰,早些动身为宜。”
见二人都这般说,应白川自然无异议:“成,那便出发罢。”
既是一同前往,应白川自乘宁王府的马车,林意则与顾放同车。车轮缓缓转动后,林意挨着顾放坐下,心中那股微妙的心虚又浮了上来,小声试探:“夫君……是不是瞧出什么了?”
顾放微微一笑,温声反问:“瞧出什么了?”
林意一时语塞,不知该如何接话。顾放见状,眼底笑意更深,轻声道:“人皆有自己的隐秘心事,再寻常不过。我并无意深究,只是……”他顿了顿,声音里掺进一丝几不可察的委屈,“只是见你与安进说着些我插不上话的体己话,心里……有些吃味罢了。”
林意听得心头一暖,又酸又软。
听听,这是什么神仙回应!既体察到她有话不便明说,体贴地借故避开,留足余地,又不曾走远,始终守在不远不近处,顾全她与外男独处的名声,等她惴惴不安时,更不着痕迹地将话头转为吃醋这般夫妻间的小小情趣,轻巧地翻过了这一页。
呜呜呜,她家夫君怎么就能这样善解人意,又这样温柔妥帖!
林意感动得一塌糊涂,拉起顾放的双手,眼里泪光盈盈:“不是我不愿说,只是……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,才能让你明白,让你接受。我怕这些事对你而言,太过惊世骇俗,反而平添烦扰。”
顾放闻言,轻轻回握住她的手,掌心温厚:“我知道。我大概能猜到几分。”他顿了顿,声音放得更柔,“所以,也请你……不必告诉我。”
“啊?为什么?”林意愣了,一时竟没细想顾放能猜到她与应白川的来历,本就是件细思之下令人心惊的事。
顾放静静望着她,目光深静如水,话里却似藏着未尽之意:“人生在世,难得糊涂。”
林意怔了怔,随即心底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敬佩。她不由朝他竖起拇指,语气里带了调侃,却也含着真心:“夫君这是……大智若愚。挺好的。有时候想想,稀里糊涂过完一辈子,说不定比清醒地走完全程,还要幸福些。”
顾放顺着她的话,温声问:“小意似乎……很有感触?”
“也不算感触吧,”林意想了想,将从前的事换了个壳子,“是我师傅曾说,人知道得越少,往往活得越容易满足。他告诉我一个故事:他有个友人,生在山野深处,拼尽全力才走出大山,见识了外面的繁华。可那人见了之后,反而觉得……痛苦。”
“痛苦什么?”顾放不解,“是因她发觉自己从未享受过山外的好日子,两相比较之下,心中不平?”
“不是的。”林意摇头,“她原本以为山里那样的生活是常态,因为人人都那样过。直到走出大山,她才惊觉自己从前过的日子是何等的困顿,而山里每一个人,都活在同样的困顿里。可山中人自己却浑然不觉。”
“所以她的痛苦,是来自看清了众人的苦,却无力改变?还是痛心于他们对苦难的麻木?”顾放试着理解这故事背后的意味,“你认为她因走出大山而清醒,所以反而痛苦?”
“差不多吧。若是从未走出,或许便能无知无觉地过完一生。”林意垂眸,声音轻了几分。
顾放偏头思索片刻,望向林意,缓缓道:“我征战这些年,见过大乾边城的百姓遭北疆烧杀劫掠,他们很痛苦。也曾有一次为追击敌军深入北疆腹地,路过一个小部落,里头尽是妇人、老人与孩童,看他们的日子,想来……也很痛苦。或许这世间的苦难本就是大多数,不分南北,不论敌我。”
“也许吧。”林意点点头,总觉得这话题太过沉重,便不再深谈,转身撩起车帘,探头向外张望。
不过片刻,她忽然缩回身子,眼睛亮晶晶地转向顾放,语气里带着压不住的兴奋:“夫君夫君!我看见上次我们散步的那条小河了!就那棵最大的树下——有一对小情侣在亲嘴!怎么上次我们就没这样干呢!”
顾放:“……”